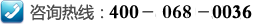

孟母三迁,成就一段佳话。而我小时候也搬过一次家,偏偏就遇到了一群“坏家伙”。 坏家伙们的聚集地是湖北省某小学一年二班。这所小学位于我家老城区,鱼龙混杂,市井气息浓厚,和我转学前就读的小学中相对纯良的孩子相比,这里的小学生性属奇葩,姿态各异。
第一位登场的“坏家伙”是泼辣的“江姐”,她之所以得了这个革命烈士的称号,纯然是沾了姓氏的光,和那位“江姐”在精神气质上并无相似之处。当我第一次在一年二班教室见到江姐时,她正带头“破坏公共财产”——切粉笔:用小刀片把不同颜色的粉笔切成细末,掺水混合,拿到走廊上晒干,制成新粉笔。
这项活动在我刚转学时风靡校园,“下课一声铃,万户切笔声”,只见一双双小手,专著地用小刀片“叨叨叨叨”切着粉笔,在桌上、在板凳上、在走廊护栏上,实乃校园一时盛景。
你完全想不通切粉笔的意义何在:新制成的粉笔一触黑板立刻粉碎,根本没法用。
很快,我也主动加入了大部队,“叨叨叨叨”切了起来。我认识了几个一起切粉笔的“笔友”,度过了转学初的关键期,现在想来,真要谢谢那一根根被我“碎尸万段”的粉笔。
从主动要求切粉笔开始,我幼时的矜持慢慢褪去,脸皮越来越厚,乐于掺和各种 “无用”的活动。其实真正切过就知道,把粉笔切成末再掺水、晒干的过程很有成就感,见证了“从无到有”,这是对人类创造欲和动手欲的极大满足。不管课程多无聊,孩子总能想到一些满足天性的玩法。
5年级,我见识了一位真正的“坏家伙”。当时,他坐在整个教室的最后,独自成排。从这特殊的座位,可看出他在我班的特殊地位,他就是头号问题学生“造爷”。“造爷”的父母都不在身边,他曾数次离家出走,不离家出走时,就借住在另一位开麻将馆的同学的家中。
他个子很小,眼神狡黠,贴在脑门上的头发乌黑多油,随时可以炒一盘小白菜。有一天中午,“造爷”穿了一身不合身的西服,戴着一只夸张的金色戒指,昂着头晃进了教室,他说自己已加入某帮派,且很为这身料子极差的西服骄傲。
对有特殊志向的“造爷”来说,加入帮派,成为混混儿是真找到组织了。他的志向很恐怖——杀人,杀某个人。那人是他的大伯,当时还在蹲监狱。多年前的一个晚上,“造爷”的大伯喝醉酒和人起了争执,“造爷”的爸爸去劝架,大伯一失手把“造爷”的爸爸,自己的弟弟打死了。
“等他出来,我肯定亲手……”我不能忘记“造爷”对我们说这事时的神情,有怨恨,似乎还有点得意。我对他既同情又敬佩,心情远超善恶是非,正、负能量。
哪怕只是个小学生,生活也可以很艰难,很不同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触到自己可见的世界是多么狭小。
自从切粉笔之后,我渐渐融入了“坏家伙们”的群体。切粉笔只盛行一时,但“包干区”却扫了5年。扫地,是“坏家伙们”每天清晨的例行狂欢,我们最擅长自己找乐。
我们班的扫地活动由生活委员匡同学统一组织。匡委员的父母在菜场卖菜,他每天早上4点种就起床,坐上小三轮跟着父母去江边渡口拖菜卖,因此到校的时间冠绝全班,负责保存班级钥匙。
印象中我只有两次比匡委员更早到校,在等他开门的时候,我看着太阳还未升起的天空,一次见到了巨大月亮,一次见到了像老花眼镜上的螺旋纹那样规整的云彩。这也是我们狂欢的活动之一:分享各种清晨的奇闻异事,有人看到过空无一人的音乐教室里彩灯闪烁,年久失修的室内篮球馆中趴着巨大的蜘蛛……
匡委员本人老实勤快,作为委员他最大的领袖才华是放任其他坏家伙们“肆意妄为”:有人用竹扫把耍大刀,有人相互比着赶灰。下雨天是最好的,好中最好的又是大暴雨,在积水至脚踝的煤渣跑道上,大家脱了鞋随便淌水,大竹扫把一挥一顿都带出水珠连连。若是赶上春天更热闹,男孩子们捡一把“杨树吊”冒充毛毛虫,吓唬女生,被吓着的女生则马上仗着小学时代更胜一筹的体格把男孩暴捶一顿,真是坏家伙遇到坏家伙了。但奇了,坏家伙们扫地的成果向来很好。
没有认识这群坏家伙,我会不会像“孟子”一样成为圣贤了?还真从来没这么想过,在小时候学到《孟母三迁》的课文时,我真实的感慨是:哎,小孟子不会有点无聊吗?
谢谢小学时代遇到的坏家伙们,我一点都不无聊,这种“不无聊”建立在“多样性”上:这里有把生命“浪费”在“无用”事情上的坏家伙,有带着悲剧色彩的“坏家伙”,有在劳动中变法嬉闹的“坏家伙”——哪怕只是个“儿童”,生活也如此层次丰富,每一个有非凡的想象力。
如今的家长[微博]依然如昔时孟母一样看重“环境”的浸染作用,所以学区房被热炒,价格高得吓人。我想这大致没错,但如果我以后有了自己的小孩,我也会让他认识几个形色各异的“坏家伙”。这样,等他长大了也许就会像我一样,不时问问自己:你还记得心里的那个“坏家伙”吗?你还记得他有多特别吗?
